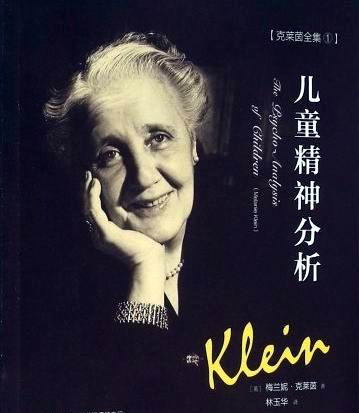
客体关系理论(object-relations theory)是心理动力取向的人格发展理论,它是由许多临床治疗家建立起来的复杂的理论体系,其基本看法是:人类行为的动力源自力比多寻求客体,重点是客体,而不是力比多满足本身。因此,客体关系理论是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中来探讨人际关系的,相对于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而言,客体关系理论更强调“关系”与“养育环境”对人格的影响,特别强调早期的母婴关系(即三岁之前的亲子关系)。该理论始终关注的是婴儿与母亲的关系发展是如何影响到自我的内在精神结构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客体(object)一词较早为弗洛伊德所使用,意指对主体而言具有价值的关系对象或满足需求的事物。因此,客体一词可与“他人”互换。客体关系意指人际关系,只不过多数情况下,客体关系并非指外部关系,而是指早期母婴关系的内部影像,或者指存在于一个人内在精神(心理)中的人际关系的形态或模式。
客体关系理论的起因,首先与该理论的奠基人-梅兰妮.克莱茵女士(1882-1960)自身的经历以及她所从事的研究及临床治疗工作有关。克莱茵一生都遭遇着各种不同亲密关系对象的丧失以及母女关系(包括她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以及她与自己女儿的关系)的困扰。克莱茵青年时代居住在维也纳,她的生活被令人窒息的母女关系所困扰,并曾经经历过一场令人烦恼的、不如人意的婚姻阴影(她遵从父命,嫁给了一个没有感觉的无趣男人),由此陷入重度抑郁。1914年前后(她32岁时)接触弗洛伊德的理论,191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一个儿童的发展》,其后在布达佩斯参加了弗洛伊德重要弟子——桑德尔.费伦齐主持的精神分析工作,并接受了另一位精神分析家卡尔.亚伯拉罕(英年早逝)的邀请到柏林,接受他的短暂分析。1926年接受弗洛伊德传记作者欧内斯特琼斯的邀请,移居到英格兰,从事儿童精神分析工作,并兼任琼斯的孩子们的分析师。1932年克莱茵写成《儿童精神分析》专著,之后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笼,直到1960年去世。
克莱茵的理论发现与她自身的家庭背景和心理困扰有密切关系,因为她终身都受原生家庭客体关系的困扰。克莱茵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是在父亲50岁时才出生的,不过在父亲眼里是最聪明漂亮的女儿。父亲原本是一名犹太法典学者,37岁时脱离正统背景开始转行当医生。克莱茵的母亲非常漂亮,精力充沛,善于持家,充满求知欲。在很小的时候,克莱茵就对母亲怀有羡慕之情。克莱茵在青春期之前便经历了一系列丧失,5岁时二姐去世,17岁时哥哥去世,18岁时父亲去世,21岁结婚,28岁生孩子,32岁母亲去世,44岁与丈夫离婚,52岁时27岁的长子登山去世,几乎是在这同一时期,她的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女儿宣布和她断绝母女关系,倒向安娜.弗洛伊德,至死没有和她和解。
上个世纪20年代末,因克莱茵与安娜.弗洛伊德在理论观点及个人关系上的巨大分歧,精神分析分裂为克莱茵的“伦敦学派”和安娜.弗洛伊德的“维也纳学派”(后者发展为自我心理学体系)。其后,费尔贝恩和温尼科特脱离克莱茵的伦敦学派,形成第三阵营即“中间学派”。这种分歧一直持续至今,应该说,直到上个世界80年代,深受安娜.弗洛伊德和海因兹﹒哈特曼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的主流思想仍然是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
基本理论观点
梅兰妮.克莱茵是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人物,客体关系的代表性人物,也是精神分析继弗洛伊德之后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家。她对精神分析思想发展的最重要且永恒的贡献,是她对于“偏执-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的阐述,揭示了母婴早期关系的真相。克莱茵客体关系的主要理论观点有:
①.儿童天生就具有死亡本能,即攻击性或破坏本能,他们的心理世界充满了原始的冲动、谋杀和自杀的愿望和恐惧,这种攻击性往往针对早期客体——乳房及母亲,并因攻击性而产生自罪感或抑郁。
②.任何内驱力和本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特定的客体相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理解为驱力是具有客体特征的,这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有区别的,也是对驱力理论的重要修正与补充。
③.婴儿一开始只能根据他所体验到的客体的“好”或“坏”来判断这个客体,虽然任何客体都是“好-坏”并存的,但婴儿往往能体验到的只是客体的部分特征,所以称为部分客体。
④.当客体引起婴儿的恐惧和焦虑时,为了防止被报复或被毁灭,婴儿就想控制甚至毁灭客体。为了达此目的,婴儿会采取内射、分裂、投射、理想化与贬抑,投射认同等心理机制,逐渐把客体的各种特征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主观意义的客体表象(意象),并建立内在主-客体关系。这个关系的状态,成为个体内在精神结构的主要部分。
⑤.任何现实人际关系上的适应困难,其实都是患者内在客体关系缺陷的外投所致。治疗的关键是在移情关系中通过治疗师的工作,改变患者内在的客体关系结构缺陷,从而达到被治愈的目标。
偏执-分裂心位
心位一词指一种内在心理状态。偏执分裂心位这个概念,用于描述婴儿最初针对母亲(母体)的两极化体验,它指针对“好乳房”的爱和满足与针对“坏乳房”的恨与攻击的不兼容体验。这个概念与弗洛伊德的生本能与死本能相对应。
在弗洛伊德看来,力比多冲动的目的是释放,客体作为满足物是被偶然发现的朝向这一目的的工具。克莱茵则认为,客体本身就预先构筑在力比多冲动体验中。举例来说,一个从没喝过水的婴儿,在她喝水之前“水”就以某种模糊的、未成型的方式存在于“口渴”的体验中。爱和保护的力比多冲动在其内部容纳和镶嵌着一个爱与被爱的客体意象;憎恨和破坏的攻击冲动在其内部容纳并镶嵌着一个恨与被恨的客体意象。因此,新生婴儿的原初体验就处于“爱与恨、渴望满足与攻击破坏”的分裂状态,而且这种体验是不连贯的。
克莱茵所说的“偏执”(paranoid)是指面对“坏乳房”的核心性的迫害焦虑,是对来自外部的侵略性恶毒的恐惧。分裂(splitting)指的是核心性的防御,对爱与被爱的“好乳房”及恨与被恨的“坏乳房”保持警惕的分隔或割裂。
在克莱茵看来,对死亡本能所引起的迫害性焦虑进行防御是婴儿的迫切需求,是偏执-分裂心位的来源,并把这一概念视为自己理论的核心。这正好契合了克莱茵本人的早期母婴关系经验,也在众多的儿童和成人精神分析实践中得到印证。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个体而言,持续终生的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偏执焦虑,或者说是如何摆脱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受到被威胁的感觉。
在《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一书中,为了很好地说明克莱茵的理论观点,列举了关于“蕾切尔”的案例:
蕾切尔,一个25岁的女招待,被两个生动鲜活的心理意象——鲜花与粪人——所困扰,无论是清醒还是在睡梦中,这两个对立的意象都始终支配着她的生活。第一个意象是一些细小的、极度脆弱的鲜花。第二个意象则是巨大的具有威胁性的人形,但没有具体的轮廓,完全由粪便组成。这两个意象以一种她不能理解的方式捆绑在一起,她似乎要急切地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会儿是鲜花,一会儿是粪人,继而又是鲜花,之后又是粪人。
蕾切尔想把这两个意象整合在一起,但是做不到。她害怕这样的整合会破坏娇嫩脆弱的鲜花,导致它们被淹没和埋葬在巨大的粪人之下,但合并的愿望随之而来,出现在清醒的想象与梦境中,形成强烈的心理冲突。
蕾切尔有一个十分悲惨的童年。在不到一岁时父亲去世,母亲身心衰弱,不能够照顾她,因此她是被她母亲的一个堂姐在乡下带大的。但这位养母性格不好,时常殴打她。一些时候她似乎很爱她,但在另一些时候,则换上了一副恶毒的、偏执狂样的面孔。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位所谓的“养母”患有精神分裂症,养母的丈夫也是一个有问题的酒鬼,无法为蕾切尔提供保护,经常不在家,感觉离她很遥远。
进入成人的蕾切尔同样处在极其分裂的自我体验中,她很多时候觉得自己充满了丑恶的破坏性,憎恨自己和周围的人,憎恨这个“狗屎”的世界。而在另一些时候,当她处在隔离幽闭的状态时(她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特别是在自己一人听音乐和读书时,凄凉、忧郁的感觉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温暖的感觉。不过,当现实生活中有某个人给她创造了这种感觉,她能被这种温暖所感动,但却感觉有某种危险要发生,因此要逃离这样的关系。
鲜花与粪人意象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体验,是蕾切尔早年生活经历的残留物。她渴望能够把它们整合到一起,渴望减轻犹豫,体会到更多的连续性,但是要在现实关系中做到这一点,就要冒失败的风险,这个风险便是,要冒着可能会激起她爆发性的愤怒和憎恨的风险,任何试图整合这两种冲突体验的尝试,都有可能要冒险破坏哪些能够短暂照亮她黑暗世界的光线。所以,让好的体验尽可能远离坏的体验,爱的感觉尽可能远离憎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她只能在远离他人并处于幽闭状态时才能体验爱与被爱的原因。
抑郁心位
从分裂朝向整合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发展倾向,这种倾向促成了婴幼儿对客体的整体感,并非全好或全坏的,而是时好时坏的。于是,婴儿开始不再感到好乳房和坏乳房是相互割裂、彼此互不相干的,而是母亲身上不同的方面,这个转变促使婴儿开始理解到母亲这个更为复杂的它者,尽管这种认识仍然是主观性的而非事实上的母亲。
在这个转变中,婴儿对他人的体验从分裂的部分客体变成的了完整客体,偏执性焦虑减轻了,个体的痛苦与挫败不再是由纯粹的恶毒和邪恶所引发的迫害恐惧,而是有“不可靠”和“不稳定”带来的安全感的焦虑。因此可以说,当婴儿把“坏的”和“好的”放置与同一完整客体时,就打碎了先前由“偏执-分裂”心位所建立的平衡。
接下来,这个完整的母亲由于不能够适时满足婴儿的欲望,婴儿就会出现了匮乏,体会到失望、愿望落空,由此引发渴望而不被满足的痛苦、挫败甚至绝望。因为是一个完整的客体(母亲),当婴儿用憎恨幻想去摧毁她时,摧毁的就不仅仅是邪恶的“坏乳房”,也消灭了提供满足和美好的“好乳房”。因此,婴儿在因狂怒幻想摧毁令人挫败的完整客体的同时,也消灭了自身的保护者和避难所,灭绝了自己所在的世界,也灭绝了这个世界中的自己,并因此感到恐惧。
克莱茵把儿童身上存在的因想象毁灭所爱的客体所而产生的恐惧,以及因自身的破坏性损害了所爱客体而带来的自罪感,称作“抑郁心位”。处在抑郁心位的儿童,会“爱恨交织”地与某个完整客体保持联系。儿童一旦因狂怒想象损坏了完整客体后,就会产生深深的懊悔,并竭尽全力去修复被损害的母亲,维持完整。
儿童对自己修补能力的信任,对于他们是否能维持 “抑郁心位”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克莱茵认为这实际上取决于儿童是否相信自己爱比恨更强烈,从而可以撤销自身破坏性所带来的浩劫。不过温尼科特则强调“真实母亲”的重要性,这样的真实母亲能从婴幼儿的破坏与攻击中幸免,并能够将婴幼儿的体验抱持在一起,相信这才是儿童信任自己修补能力的前提。这里的“真实母亲”可以理解为那个存在于母亲身上的、不受虚假人格左右的纯粹的母亲。
如果儿童不能维持抑郁心位的平衡,就不得不选择卑微地依附于这个完整的母亲,因为她不可替代,因而必须承担焦虑性抑郁的痛苦。在此情形下,儿童的另一种抵御抑郁的方式是“燥狂性防御”,在这个状态中,客体的独特价值和对客体的依赖性被不可思议地否认掉了:“管他的,谁会需要这样的一个它者呢?母亲、父亲、爱人们都一样,对我来说得来全部费工夫!没有了谁,我都照样生活,肯定会过得更好!~~~”通过躁狂性防御,儿童将自己凌驾于客体之上而获得自我慰藉,但这种慰藉注定是短暂而虚幻的。
克莱茵并不关注如何走出抑郁心位,因为这涉及到如何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的对接问题,这一点是她没能完成的理论整合。相反,克莱茵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阐述,感觉是含混不清的,有刻意修正正统理论的嫌疑,这可能有其自身的缘由。所以,克莱茵眼里所谓相对健康的状态,不过是不断丧失而又重新获得心位的过程,因为爱与恨是人生的主题,抑郁性焦虑是人类存在的恒常和核心特征。
回到蕾切尔的个案,只有蕾切尔相信鲜花能够从粪便下面再度出现时,鲜花和粪人才能够整合在一起,走出偏执-分裂心位。不仅如此,她还相信,粪便还能够为鲜花的茁壮成长提供养分,而不是埋葬了所有的生机,才能维持一种抑郁心位的平衡。
就爱的体验而言,“偏执-分裂心位”的爱是纯粹、脆弱而稀薄的,尽管这种爱的纯净性常常为患者所赞美。而“抑郁心位”的爱在破坏性的恨和修复的爱的循环中被调节,更深沉、更复杂、更真实,也更富有弹性。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只有相信了母亲是时好时坏的,而不是全好全坏的,才能走出“偏执-分裂心位”;一个人只有接受了母亲的时好时坏,并不再保留对不完美母亲的愤怒与攻击性,才能最终走出“抑郁心位”。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信念——相信爱,相信爱能够吸纳攻击性的能量,并能避免被恨所淹没。
(南岛/向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