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欧洲回到东亚,回到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
在那个大时代里,蒙昧和觉醒并存。各种思潮,文化的、政治的、科学的、伦理的、军事的……纷纷涌入,成为救国图存的养分。正如若干年后,那部《霍元甲》的主题曲所唱的:“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

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算是大时代里的小学问吧,也借着西学东渐,开始传播进来。咱们走马观花,理一理这笔流水簿子,虽或稍显平淡,想来也自有其别样的况味。
据考证,1872年11月28日,署名“执权居士”的中国人在《申报》发表《论西教兴废》,提到西方“化学、天文、格物、心理”等学问,这是首次在中国用“心理”来代指一门学科。不过始终没有人能考证出“执权居士”何许人也,这个词像是偶然一用,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

一般认为,Psychology在中国被译作“心理学”,且广受关注,是在30年之后。那时节,日本用汉字“心理学”翻译了Psychology,由康有为在1897年带回中国。到了1902年,梁启超专门撰文区分了“心理学”和“哲学”,王国维则翻译了日本的《心理学》一书,就把这个词推而广之了。
1879年,在“执权居士”之后7年,有一个德国人,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实验室,这被认为是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标志。当然,这个人就是冯特。

此后约40年,冯特的一位中国学生,在1917年的北大,支持陈大齐在哲学系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他是蔡元培,当时的北大校长。
这个时间里,一战已经结束,西方暂告平静,东方却依旧水深火热。时光前行到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继续蓬勃展开,大幕后边的新时代,一时还看不清楚。
这时候的老弗爷在做什么呢?这时候弗洛伊德已经赶走了“叛徒”,距离得口腔癌还有四年,距离希特勒上台排犹还有14年。这一年他的世界影响力继续扩展,还创办了“国际精神分析出版公司”,负责出版自己和精神分析运动的相关著作。这大概算是弗洛伊德“最好的时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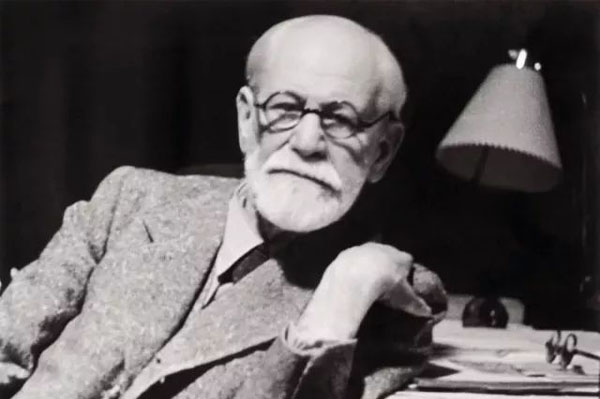
而作为一种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弗洛伊德的学说这时也已经在国内传播。只是这时候,国内似乎还没有开拓出心理咨询或者治疗的理念——那要等到1935年之后,沙利文的中国学生戴秉衡回来之后了——精神分析主要作为一种个性解放的理念被重视,和进化论、超人学说等被一起注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
1922年,鲁迅创作了小说《不周山》,目的是借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创造的发生,人和文学的起源。换句话说,就是用性本能、性驱力的理论,来演绎中国的“创世纪”,演绎繁衍、创造和升华。带着这个前提,去从动力学的角度来看下边的引文,“懊恼”、“不足”、“弥散”、“无聊”、“圆满”、“肉红”……这些词里,是可以读出满满的力必多的味道的。说不定,作者在家庭和婚恋方面的苦闷和驱力,也在这样的描写中,像写诗一般的描绘了出来。

伊似乎是从梦中惊醒的,然而已经记不清做了什么梦;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得有什么太多了。煽动的和风,暖暾的将伊的气力吹得弥漫在宇宙里。“唉唉,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伊想着,猛然间站立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向天打一个欠伸,天空便突然失了色,化为神异的肉红,暂时再也辨不出伊所在的处所。伊在这肉红色的天地间走到海边,全身的曲线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浓成一段纯白。波涛都惊异,起伏得很有秩序了,然而浪花溅在伊身上。这纯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动摇,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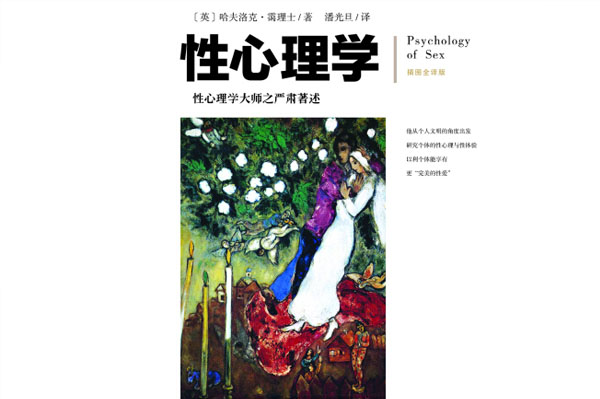
不止这篇,鲁迅还有不少文章中体现出来对潜意识、压抑、意识流等理念的借鉴。也在一些杂文里不时有对弗洛伊德和他的泛性论的直接评论和批评,可谓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了。有一本书叫《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里边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文章,要么是鲁迅自己的文章,要么是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可见鲁迅在文学创造中和弗洛伊德纠缠之复杂。相比之下,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则对弗洛伊德提及不多,但周作人可能是中国最早宣传性心理和性教育的学者,对霭理士和他的《性心理学》甚为推崇。
时光之舟继续前行,到了1930年。章士钊翻译了弗洛伊德的自传,还在书中影印了弗洛伊德写给他的亲笔信。其他学者也在不同时期,做过对精神分析传布的工作。

比如美学家朱光潜就翻译、介绍了很多弗洛伊德的、荣格的心理学的知识。这些学者们触类旁通,觉得可能有益于时代,就尽量接引进来。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学者中,对精神分析方面研究较多的是高觉敷。他翻译了《精神分析引论》等弗洛伊德的专注,并正式把这门学问用中文翻译成了“精神分析”,那个“伊底”的译法,也是他发明的。高觉敷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并不认可,但依然作为一种有创造性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理论来推荐。
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待西方学问的基本的态度。既不弃如敝履,也不迷信盲从。只是如盗火之人,“用他国的火,煮自己的肉”,尽力而已。






